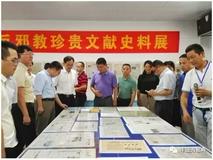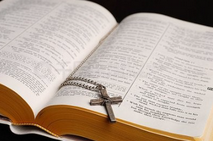笔者在大学学的就是历史专业,加之从小就爱历史,所以对教会的历史特别重视。在走访400多个教堂的过程中,几乎每到一地,都要采集信息、收集资料和史料以用于撰写教会的历史,这些教会历史文章包括人物见证和历史事件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这几年教会历史的文章也发表了有130篇以上。
根据德尔图良的法则(Tertullianus,全名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us,是基督教早期最重要的神学家和护教士之一,生活在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约155年–220年,被誉为“拉丁基督教神学之父”),“先出现的事物总比后出现的事物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他的说法是真的,那么教会了解历史就变得十分必要,那样才能知道什么是先发生的,什么是后发生的;因此,古代的作者称‘历史(historia)‘是时代的见证、真理的光芒、记忆的生命、生命的教师,以及古老的显示,等等。不知晓历史,我们的人生便是盲目的,很容易陷入各种错误的泥潭。”—约翰·福克斯(John Foxe),《殉道史》(Acts and Monuments, or Book of Martyrs)
对于德尔图良这位基督教先驱有争议的地方我们暂且先不去研究,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历史不能丢掉。特别是基督教在本地,甚至是本县、本镇、本村、本街道的历史,尤其应该收集、整理、挖掘,留存下来,这样才能无愧于先人。
写教会历史,这是我一个神的文墨苦力这几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是无愧的——尽管我做得不太好,但我真的是用我晚年的时间在竭尽全力地去做。虽然这很艰难,有的时候为了考证一个基督教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我需要翻阅30多种资料和书籍、著作,每次去一次图书馆要倒三次车,最多的写了四万多字。这也是我和许多教会传道人牧长在关心和探讨的事情,关于如何留存住教会的历史、“抢救”基督徒,包括老传道人的见证。有许多的同工同道跟我有一样的想法:要挖掘教会的历史、要保留本堂、本地教会的历史。不能让历史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湮没了,那不仅仅是遗憾的问题,实际也是我们对不起先人们,也是一种严重的过犯。
对此,我曾经在福音时报写过文。那么这次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撰写教会历史包括见证方面的引用史料的话题,属于“实战”。不是“应该怎样写教会历史”的抽象理论,而是“我到底怎样把一段史料真正写进文章、讲章、见证、展板甚至短视频”的实战。理论全网都是,买两本书也能翻个遍,可一到动手就卡壳:这条口述史敢不敢用?那张发黄照片放在首页会不会侵权?老人方言录音里提到的“义学”到底对应今天哪条街?怎样把散落在中国大地,尤其是本乡本土的基督教“碎片”整理、编辑成福音的历史进程。
此次和各位分享的主要议题就是搜集、整理、挖掘、引用中国基督教(尤其是本乡本土基督教)历史资料的意义,把分散的、碎片化的教会历史编辑、整理、发表,这既涉及对我们的教会自身发展规律的总结,也关乎对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理解,更指向未来教会发展方向的探索,其意义重大。
一、搜集史料是历史认知与文化传承
编写教会历史,特别是本地本堂教会的历史,还原真实历史图景是一件费力并不讨好的事情。说一句得罪人的话:大多数的牧者不乐于去做这件事情,只是安于现状。
编写教会历史首先的是要收集、采集资料。以史料为依据、以事实为依据,才能写好教会历史。写教会历史,不能凭着主观臆想、不能胡编乱造,也不能听信那些野史或者传说。
1.纠偏纠错:通过采访信徒、传道人、查阅档案和地方志等,系统梳理史料,可纠正外界对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片面认知(如简单标签化为“洋教”、“侵略”或“殖民工具”等),展现其从唐代景教至今的复杂历程。例如,景教通过融合佛道术语实现本土化,体现早期跨文化对话的智慧;基督教对于中国西医的贡献等。
2.保存集体记忆:挖掘地方志、地方教会档案、传道人或信徒、家属的口述史及实物遗存(如古碑文、教堂建筑、笔记、日记、老的圣经等),有助于构建完整的历史叙事链条,传承基督教历史遗产,避免因时代动荡导致的文化断层。这些东西有很多是散落于民间,有的是老的传道人和信徒不在的,其后代也不信主,放在他们手里确实有被毁掉的危险。我们应该尽量动员他们的后人把这些东西交给教会保管。
3.激活基督教文化基因:研究基督教历史、基督教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有文化现象(如方言圣经、本土神学思想),能够为中华文化多样性提供新的视角。例如,苏州话方言圣经的版本差异反映了吴语演变与本土化策略的结合;蒙古族语版、苗族语版的圣经启示我们基督教与中国少数民族的融合。
4.赋能城市更新:如一些城市通过百余年基督教文物,整合基督教历史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的提升动力,既保护文物又赋予其现代功能。比如辽宁大连的北京街教堂、黑龙江哈尔滨的索菲亚教堂等。
二、搜集史料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意义
基督教是普世的爱、福音也是传给普世的。基督教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会促进基督宗教和谐与社会稳定。如:
1.化解误解与冲突:通过展示基督教在教育、医疗、慈善等领域的贡献(如创办大学、设立医院、提倡妇女解放、参与救灾等),可改善公众形象,缓解因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矛盾。
2.助力政策制定:教会档案中关于产权纠纷、管理模式的历史记录,能为现行宗教事务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治理经验。这些历史资料比较详细的记载了老的基督教堂在当时的教产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有的还包括房契、地契、建筑档案等等,有助于落实政策收回教产。
3.增强文化自信与软实力:教会史料中蕴藏着大量基督教中国化的生动案例:从利玛窦穿儒服、译经典,到当代吴耀宗提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神学院用古琴谱赞美诗、用茶礼诠释圣餐,既坚守信仰内核,又主动融入本土语言、伦理与美学,彰显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与创新能力。系统搜集、整理这些文献与口述史,提炼“相遇—对话—共生”的叙事框架,通过多语种纪录片、数字博物馆、社交媒体短剧等形式向海外传播,可让世界看到中国并非“信仰沙漠”,而是各文明互鉴、共创的沃土,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中树立开放、自信、可敬的国家形象,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提升文化软实力。
4.突破照搬模式:基督教“三自原则”更以组织自立、自养、自传,切断殖民脐带,奠定中国化根基,足见脱离本土文化肌理之传教难长久。今日城乡发展失衡、境外渗透暗流,正可从史料提炼预警机制:如民国“自立会”以教产登记、本地牧养抵御外资操控;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会和基督徒、传道人的爱国运动;乡村布道团以医卫、农技嵌入社区,减少依赖。创造性转化神学思想,把“敬神爱人”接入中国本土,实现中国基督教的健康传承与社会的双向奔赴。
5.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史料彰显中华文明包容性,大量的基督教历史资料证明,基督教在中国是多元共生典范。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外来宗教可通过主动调适融入中华文明体系,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即基督教中国化。中国基督教的处理方式(如三自原则)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宗教本土化的参考样本。
三、如何引用史料
1.写作历史文章的核心原则:史料优先,论从史出。
“史料优先,论从史出”是历史写作的铁律:先穷尽档案、实物、口述等第一手材料,去伪存真,再让解释从证据缝隙里自然生长,而非预置结论、剪裁史实;材料不说话,史家只做“翻译”,凭时空排序、多重互证呈现因果。凡无证据处即存疑,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杜绝以论代史、以今律古,方能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使文章经得起时间检验。
历史文章特别是基督教史,尤其是中国基督教新教在本地、本堂的历史文章是比较难写的。这里面需要下功夫大量地查阅史料、查阅原始档案、查阅有关专著、走访有关人士,实际上是一件艰苦的文字事工。但是“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必须在浩瀚的史料和专著中竭力挖掘基督教的历史,特别是基督教在中国、在本省、在本市、在本县、在本区、在本乡本土的历史,尤其是后者非常重要,因为世界的、中国的基督教历史文章有很多,真正需要挖掘和保留的就是后者。而这些历史大多数已经被淹没了。在我的实际采访和写教会历史的当中,发现有的教会自己有100多年的历史,而负责人居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去研究、不去探讨,也不去追溯,有的不知道从何处着手,所以把教会的历史“丢掉了”,甚至有的教会把保存近百年的历史资料,文字照片都送给了别人,而自己手头什么也没有了,真的可惜!
2.历史研究的根本目标是还原过去真实。其方法论基石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傅斯年语)。这意味着:史料是历史叙事的唯一合法来源,任何脱离史料的“创作”都是对历史的背叛,那就是“伪史”。梳理史料本身即是靠着圣灵带领和自己的知识面的研究过程:通过对比、考辨、整合碎片化记载,发现被遮蔽的联系或因果,这种“编辑整理”、“提纲挈领”绝非被动摘录,而是主动的认知重构;如果要求对写作历史文章限制摘录的历史资料不能超过百分之多少,对于写历史是有点难了。历史就是要从浩瀚的史料里找到本来的面目。它不同于一般的文章,一般的论文等,可以要求引用的资料不超过多少,防止抄袭。但是写历史就是要通过大量的史料来编辑整理、梳理、发现,而不是自己在那儿“创作”,在那胡编乱造历史,不是靠个人“发挥”,那就是不尊重历史了。至于自己“创作”空间仅存在于史料空白处,且需以“合理的推测”形式呈现,并明确标注其假设性(如“或然”“可能”)。例如,司马迁写《鸿门宴》人物对话,虽无实录,但符合楚汉之际政治逻辑与人物性格,这种“创作”是史料缺环下的情境还原,而非凭空想象。
3.引用史料要根据实际情况。当然,以引代论,大段堆砌原始文献却不加分析,让读者看不到清晰的历史脉络,也是不正确的。核心要求是“对史料的深度加工”:即使引用50%以上的原始材料,如我们国内的历史权威期刊《历史研究》、《考古》等。只要通过校勘、辑佚、重新断句、跨文本比对如对比《汉书》与《史记》对同一事件记载差异,揭示出新材料,如“班固如何系统篡改汉武帝形象”,仍符合学术规范。此时“引用比例”退居次要,关键在于是否产生新的历史认知。“史料为骨,逻辑为血,合理推测为神经” 学术规范反对的是“被动引用”而非“主动使用”:若通过批判性整理,使史料产生新意义,即使原文占比50%以上,仍是顶尖研究;简言之:历史写作的限制从来不是“引用比例”,而是“是否允许史料自己说话”——优秀的史家如同侦探,让沉默的史料在严谨的逻辑下开口,而非替它们编造台词。
4.注意史料的“深度加工”和“甄别”。即不是把史料藏起来,而是把它“磨”成放大镜,让读者在同一则材料里看到你才看得见的一道“裂缝”,只要这道“裂缝”可验证、可复现、可追责,无论原文引用比例是5%还是50%,都符合学术规范;同时还要注意有些史料不是正史而是野史,例如《清朝野史大观》等,野史和演义题材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比如三国时期的历史专著主要是《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当然也有例外,但是要说明出处。
前提是你“引用”要得当,合理引用史料 ≠ 抄袭。
在历史题材写作中,史料引用并非存在“不超过多少”的问题,而是“必须足够且恰当”。与一般文章相比,历史写作确实允许——甚至要求——更高比例、更密集的引用,但需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比例无上限,但有“功能阈值”
这是指一条界线当身体或系统的某项指标低于它时,还能正常“工作”;一旦跌破,功能就突然下降甚至停摆。它强调“刚好维持运作”的临界点,而不是生理极限。引用史料和这个有些相似。史料的引用无硬性比例限制,学术期刊(如《历史研究》)常见单篇论文脚注占比30%-50%,《考古》学术杂志部分考据文章甚至更高。关键在于每处引用是否服务于论证、服务于历史本来面目。历史写作中,引用比例不是“多少”,而是“是否抵达真相所需的最低证据量”。读者不会计数脚注,但会感知“每一条论断是否被史料强制锚定”。当删除任何一条引用都会让论证像“多米诺骨牌”抽走一块即“倒塌”,即达到历史写作的理想密度。
第二,史料的性质
史料,如《史记》等二十五史,包括《清史稿》、《明实录》、档案、碑文等属于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或历史文献,其本身不受版权保护。你不会因为抄了一段《史记》的文字而被判定为“抄袭”,因为司马迁不可能来告你侵权,国家版权局也没有这种申报。
第三、学术规范要求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加说明地照搬史料内容。在学术写作中,即使你抄的是《宋史》、地方志,如清朝光绪年间的《铁岭县志》、1921年版商务印书馆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等,也必须注明出处。否则就是学术不端,属于剽窃他人劳动成果,哪怕是古人的,也要尊重学术传承,是吧?
基督教是历史性的,因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在我们的历史中行动。并且历史资料是媒介,通过它上帝成就了祂的作为,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包括本地、本堂的教会历史、人物传记、见证等联系在了一起。
“基督教的所有信息都根植于上帝作为以马内利的独特事件中,这意味着基督教历史正是一个获得、传播和更新使徒最初的福音的过程。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更新的过程与过去的教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D.H威廉姆斯:《重拾教父传统》第7页)
搜集、整理、挖掘、引用中国基督教,尤其是你本乡本土的史料,不只是“怀旧”,更是“认祖”与“寻根”——认信仰的祖,寻福音的根。把根挖出来,不是为了摆在博物馆蒙灰,而是要让今天的弟兄姊妹摸到纹理:原来这城、这乡、这教堂、这条河,甚至是刻着“1919年圣公会”老椅子,都是见证。早就有前辈为我们祷告过、流泪过、坐牢过、欢呼过、殉道过,从而知道经历怎么样艰难险阻,才有我们的今天。
应该说(不包括我),在那些奔跑于各个教堂、图书馆、档案馆,不辞辛苦钻在故纸堆里头,寻觅传教士、基督徒、传道人、教会的人中,有时候被冷眼拒绝和误解。而这些查找、保留史料的人是可敬的。愿我们写下的每一段文字、扫描的每一张照片、签下的每一份授权书,都成为基督的荣耀、后来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总之要想写好中国基督教教会历史,就需要我们不辞辛苦下功夫,去收集那些资料,将历史资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基督教在我们中国本地的历史展现给世人,也是荣神益人、爱国爱教的传承。
老弟兄我不是什么历史专家、学者,只不过是一个平信徒,爱好历史的人而已。以上写的这些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所学的知识一家之谈,难免挂一漏万,所以敬请各位同工同道不吝赐教。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